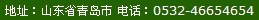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他们是我们饶河农场的建设者。这片土地上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生命轨迹从此改变。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 在畜牧连的记忆 李汉军,男,北京原子能研究院子弟中学届毕业生,年8月到22团畜牧连,年4月调二十连,一直在农工排,年12月返城。年5月--年2月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先后任工人,助工,工程师,高工,年2月退休。 难忘的失落 年8月,我们来到北大荒。在北京时,接我们的人里有现役军人,告诉我们22团在珍宝岛地区,战备比较紧张。马上要组建值班连队,战时拿枪打仗,平时生产。带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美好憧憬,高高兴兴地到了饶河。 我和一些同学被分在了畜牧连,畜牧连紧靠饶河县城,过去以养殖为主,耕地不过三千亩。还有一些同学分在了老连队一连,上万亩的耕地,分一连的同学们一来就投入了艰苦的大田劳动。每到畜牧连来都会诉苦,他们很羡慕我们小连队的环境,我们也觉得挺荣幸。再说我们离江边最近,组建值班连队时,我们应该发枪。对我们十六七岁的男孩来说,到边疆能扛枪一直是心中的渴望。 随着边境形势的紧张,各种备战工作全面展开。连队家属要撤离一线,我们奉命到距饶河县城40里路的山上建三线房,也就是盖马架子。山上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砍树扛木杆,利用草皮垒墙,虽然很累,想到这是备战需要,正是锻炼我们的时候,每天也都是任劳任怨地在山上卖力气。 一天,有同学下山回来说值班连队已经组建了,没有畜牧连。一连、二连、三连都是值班连队,一连的同学大部分都在里面,已经发枪了。听到这些,我们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人家才像个兵团战士,有枪,多带劲。好在我们连好几个同学在一起,只有互相安慰一下,平息平息心里遗憾,甚至说些葡萄是酸的话,其实心里渴望更强烈。 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山上的公路边割草,每人腰间系着麻绳。有同学说:“听说值班连队的阵地就在这边山上,是过去小鬼子的工事。这些天他们在阵地和连队之间搞拉练。”说话间,一首滔滔的乌苏里江,英雄的珍宝岛的歌声飘过来。扭脸望去,怎么那么巧,正是值班连队的战士拉练向我们这边走来。走近看时,发现是一连的队伍,个个英姿焕发高唱着歌曲,穿着统一配发的兵团军装,扛着枪,腰扎武装带,真是精神。再看我们,手拿着小镰刀,身着便服,腰扎小麻绳,站在路边。那场景就像电影里老乡看到子弟兵的到来,只是老乡是兴高采烈的,而我们是酸溜溜的。一个同校同学在队伍里先走过来,微笑着向我们摆摆手。实在是太刺激我们了,我们不由自主地随手把小镰刀扔到背后,赶紧又把腰间麻绳也解开扔到草地上,太不愿意让队伍中后面的同学看到我们是这样的“落魄”。目送走了一连队伍,我们已经无心割草了,坐在地上体会五味瓶在心里翻腾。有同学提出应该申请调到值班连队,但是哪有那么简单。这种失落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这种心情估计值班连队的人不会有,一连的同学也一直不知道我们把小镰刀扔到背后的动作。有老职工安慰我们,说是真打起来,值班连队比咱们危险,可那时就是喜欢那种危险。 随着岁月的流失,我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了,已经不认为枪有多大吸引力。那年我和连里一个知青在西通招待所常住装车,赶上团里军训,连里让我们参加在西通的军训,参加一天后,连里说晚上还要装车,我们立刻退出了军训。 回想过去,懵懂的年轻经历有不少难以忘怀的事,反看那时觉得有点好笑,但当初的情感是真实的。 紧急集合 说起紧急集合,真是心有余悸。年边境形势紧张,连队三天两头地搞紧急集合。半夜睡得正香,一阵哨声把你惊醒,赶紧穿衣戴帽,打背包。迷迷瞪瞪地出去野地转一圈回来再睡,哪还睡得着。我们连虽在江边,但不是值班连队,训练有什么用实在说不清,反正到后来大家都有些神经过敏了。睡得好好的,有人突然坐起来愣说哨响了,宿舍人一起侧耳,没有吹哨啊,于是埋怨着又躺下了。有时,在你又躺下睡着时,哨声真的响了,急忙忙又是一阵折腾。年纪轻轻,睡不好觉,活又累,感觉压力真是很大。于是有人想出各种办法应对紧急集合。首先是打背包,有两个被的,可以打好一个预备着,不过有两个被的很少。有的就把大衣冒充背包。打背包要求三横压两竖,也出现了很多种快速方法,十来秒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不脱衣服睡觉,如果有人知道半夜有活动,那干脆就不睡等着了。现在的印象中有两次紧急集合不容易忘记。 一天半夜,集合哨声突然响起,慌乱中穿上棉袄背着包就跟了出去,结果穿衣时没穿秋衣,贴身就一个背心,我的那件小棉袄没扣,是个铜拉链的,铜拉链贴在胸前冰凉,我只好用一只手把拉链拽住不让它贴身。队伍在稻田地里行进,走得很快,后面一直小跑着往前赶。天黑,路不清,我脚下一绊,一下摔倒在地上,手没来得及支撑,胸口正磕在稻田埂上,一下子上不来气,难受异常,要起又起不来,想叫身边人又说不出话。好不容易发出点声,同学王三听到,回走几步把我拉起。站起之后,总算上来了这口气。回到连队,卫生员给我检查后说可能肺部受到震动了,休息休息就行了。从这以后,棉袄不敢用金属拉链了。 由于紧急集合太多,可能是兵团普遍问题,对知青身体成长不利,上面下来个文件要求停止这样的训练。知道以后要不搞了,真是谢天谢地,犹如解放一样可以睡个踏实觉了。没想到,我们连又搞了一个逼真的大演习。出此损着的是连队周指导员,周是转业兵,平时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个头不高,胃病手术切掉三分之一的胃,吃着连里的小灶。他白天没事,设计了最后一次紧急集合。 那天夜里,集合哨响起,大家立刻忙乎起来,来到屋外,可巧江边方向也有探照灯晃动,连里传达说,边境上要有战事,我们马上后撤,说的和真事一样,要求伙房带上粮食,锅灶。马车爬犁尽量多装东西,连猪号的小猪仔也装麻袋里带走,匆忙当中很多人信以为真。队伍出发来到公路上后,发现公路上静悄悄的,不像有事。没走多远,传来命令,警报解除,返回连队,原来又是场演习。好在这是记忆中的最后一次了。 因为紧急集合,有些知青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前几年看到一个北京女知青回忆,她现在不穿袜子睡不着觉,当初就是怕集合来不及,干脆不脱袜子睡觉成了习惯,脱了就不踏实。现在别人说起来是个笑谈,但当事者的切身体会是苦涩的。 钐刀打草 在北大荒用钐刀打草那可是技术活,没有十天八天体验,掌握不好要领。 钐刀据说是源自俄罗斯,弧形的金属刀长约90公分,木制的刀杆有两米多长,刀杆的中间绑着用粗柳条弯制的刀把(供右手握持用),与传统小镰刀相比,工作效率很高,钐刀抡起来一刀能打草近两米长、二三十厘米宽那么一块面积。钐刀刀口极为锋利,用含铅的钢片制作,刀刃是用小锤把刀的边缘敲得很薄,我们叫颠刀。颠刀的技术含量很高,敲得好,刀耐用轻快,敲不好,刀片不平变形,切草费劲。开始我们颠刀都是一个老职工帮着做。 连队每年要打马草,预备冬天喂牲口。马草是在草正绿的时候将其割下,晒干,码垛。打草计数单位叫胳平,就是两个人对站抬平两臂,两人手指能相碰,在两人手臂下的空间堆满晒干的马草,这些草的量就是一胳平,要求每天每人打草六胳平。胳平的叫法不知在多大范围内使用,也不知谁发明的方法。我们打的马草主要是小叶章,这种草在东北很多,用途可以作饲料,盖房,脱坯等,在北大荒好像离不开它。 头一次看见钐刀,形象地说就是大镰刀,使用时站立,左手握杆在上,右手中间握把,打草时两臂腰部协调用力,是个很费劲的力气活。我们班八九个人,加一个老职工,开始用时,打不了几下就累得够呛,草岔高低不平,老职工教我们要领,慢慢地入些门道。打草时几个人前后排开,场面还是很壮观的,推过去身后草倒一片。打得好,草的倒向一致,看着很舒服。当然,最舒服的时候是,满头大汗时,一阵小风刮过,凉快。在野外,蚊子很多,尤其是阴天时,有时用避蚊帽,但避蚊帽感觉有些闷,用的不是很多。蚊子喜欢落在肩膀上,或者大腿外侧,曾数过一巴掌打死五六十只蚊子。在草地上,还有就是草爬子很厉害,咬上你不知道,发现时它吸了你好多血。我们每天去草场打草,累而快活。最喜欢中午晴天有小风,蚊子少。我们中午带干粮,野炊之后可以草棚躺会儿,也可以江叉里游泳。天津的兄弟常利用中午时间洗洗衣服,洗完铺在草地上,没多一会衣服就晒干了。 使用钐刀也是很危险的。当一个人跟一个人排队打草时,一定要拉开距离,太近容易搂着前面人的腿,所以都是打得快的人在前。钐刀有时也要用砂石蹭一下刀刃,刃口很长,不注意也会划着手,我的手腕处现在还能看出个伤疤,就是那时划的。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痛的是我们班张荣金受伤。 一天下工回来的路上,荣金扛着钐刀,刀片搭拉在屁股后面。正确的扛刀方式应该是扛在手把位置,刀会离身体远一些。过一个水沟时,荣金脚一滑摔倒了,大钐刀一下插入了他的屁股,随着荣金的叫喊,鲜血从他的身上喷出来,立刻染红了衣裤。大概他能感觉到鲜血外喷,一个劲叫我们“擒住!”薛锦忠使劲地掐着他的大腿根,但根本不管用,血不断地喷涌。由于血流得太多,荣金叫喊,说他非常想喝水,趴在沟边就要喝那浑水,大家拉住没让他喝。看他流那么多血,我都有点头晕。过了一会儿,卫生员赶到。他把整瓶的止血粉倒入伤口,那血慢慢地止住一些。 连里用医院后,医生整个手指伸进刀口清理,可见扎进的深度。医生说还好,差一点就是重要位置,否则荣金遭的罪会更大。医院再看他时,他对我们还露出笑脸,这让我们心里安慰一些。出院后他在连里养伤,连里要按病假给他记考勤,还要扣工资。明明是工伤,连里说是因他没按规矩拿刀,是自己的责任。对此荣金很是生气,后经班长与连长协调,整个过程就按出勤对待了。 我在北大荒打草的次数很多,水平还是不错的,钐刀给我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前些天看知青照片选,看到两张知青带钐刀的图片,虽能看出是摆拍,但那情那景仍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李汉军赞赏 长按广西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哪最好
|
当前位置: 饶河县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18在畜牧连的记忆
时间:2018-11-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省内新一波招工潮500多个名额,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