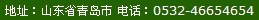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饶河农场 峥嵘岁月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系列 饶河农场历史沿革 年3月,将原八五九农场的畜牧场、二分场及八五九农场西通分场和富饶农场与人民公社插花地带的3个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队合并而建立,组建国营饶河农场。 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随王震部队第2军第三师二十二团番号编为第三师第二十二团,简称二十二团。 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农场体制,场部所在地欣城,因西靠矢山,故更名为万山红农场。 年,恢复饶河农场名称。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系列 ○ 我们的老大哥 ——悼念挚友许春青 李向东 10月16日早晨,八点多钟,宝宝打来“李叔啊,我爸没了!” “你爸怎么了?” “我爸没了!”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忽然明白过来:“什么时候?什么病?是做手术了吗?” “不是,是心衰!” 泪水一下子弥漫了我的眼睛。我即刻买好次日去往哈尔滨的火车票。无论如何,要最后再看他一眼。 今年盛夏,7月间,我陪清华大学一位好友,去北大荒转了一圈,回到哈尔滨挂电话,他家里老是没人接。我暗想:医院了!打通宝宝的手机,果然不差。 次日一早,我乘坐68路公交车去看他。 省医院住院处是一幢陈旧的老楼房,他那个病房的结构很怪,进门是一个小间,住着一个病人,里面又有两扇门,通往两个小套间,胖子住其中一间。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很亮,但走进胖子的病房却感觉光线暗淡,他那间病房朝阴。 一进门,大嫂就告诉我:糖尿病足,要截肢,外科大夫一检查,说有严重冠心病,不敢做,怕死在手术台上,这又转到心内科来。 听到截肢两个字,我心里腾起一股悲哀,不由想起老毕(毕坚由),他就是糖尿病足,截去一条腿,在床上躺了好几年,凄惨地死去。我不无凄凉地说:老胖子啊,你咋整的,你这身体咋这样了呢?他说,那有啥办法! 老胖子躺在床上,让我看他的脚,我匆匆扫了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恍惚间,看到他右脚趾上裸露的鲜红伤口,和床单上的斑斑血迹。我感到一种恐惧,说:太惨了,我不敢看! 他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我:你啥时候走? 明天。我要赶回去参加一个旅游团,去西藏。 他有些惊讶:去西藏?你身体行啊? 反正比你强。 大嫂说:”老胖子老说,赵志川、李向东,过去身体都不如我,现在他们倒都好了。“ 两三年前,青藏铁路刚通车,老胖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哎,现在能坐火车上西藏了,咱们去一趟啊?我惊恐地说:你胆子真不小,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还敢上西藏?我可不敢去! 现在我要上西藏了,他却不再提了。 老胖子的心够野的,胆子也够大的。前年五一节黄金周,他应唐伟之邀,一家三口去了趟湖南,走了张家界、凤凰、长沙。行前他来电话,约我同行,我说,我可不敢去,黄金周,旅游点风景区,人都跟粥锅似的,你走道不利索,还敢出远门?我劝你量力而行! 他去了。有天中午我给宝宝的手机打电话,问她:你爸咋样啊?他接过手机说,还行,出了点小毛病,没啥大问题。 还有一年的春天,他们一家又去了无锡、上海,在上海受到炳华、立明、柏生等战友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我和胖子一直有个心愿,期盼着哪年夏天能一起出去旅游,那一定会是一次欢乐的出游。去年9月我到哈尔滨,说明年夏天想去海拉尔满洲里,他立刻来了兴致:唉,伙计,到时候咱一起去呀!今年夏天见了面,他不提这个话题了。他知道自己走不动了。 回到北京,我一直惦着他那条腿,打过几次电话,他说出院了,回家了,争取保守疗法,后来又说,伤口有慢慢愈合的趋势。我以为他可以躲过那一刀,暗自为他庆幸。国庆节前,在北京街头,意外巧遇张景龙夫妇,我们都喜出望外,我说,请你们吃饭!找了一家好一点的馆子。席间我问起胖子情况,景龙说来北京前,与唐伟、杨永平去看过他,不但还得截肢,而且截的部位比上次还要高! 正为他的手术担着忧,谁成想,就传来了心衰去世的消息呢! 和谐号动车,干净而舒适,偌大车厢里只有十几个乘客,我找了个靠窗的安静位置坐下。车窗外的景物风驰电掣般驶过,我内心里回想起四十年来与胖子交往的一幕幕往事…… 初见胖子,是年春节前后,乌苏里江畔,寒冬时节。 我们十一连,地处从饶河到新团部的要道上,那些年,饶河冬天的风雪很大,常常把道路掩埋,团部到饶河之间也没有班车,交通很不方便。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饶河方向远远走过来一个人,面色红润,大步流星,渐渐走近,呼出的哈气在皮帽子上挂了厚厚的白霜,健壮的体型像一头熊!四十年前许春青的模样,至今还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他在我们连吃了饭,又雄赳赳地大步流星赶往团部去了,此时天色已黑,而那段路大约还有二三十里,路两边全都是黑黝黝的树林子。 我可知道走夜路的滋味。那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也是冬夜,我去十连传达兵团积代会回来,从十二连路口下了车,一个人往回走,老觉得后边有人跟着我,心里一阵阵发毛,不时地回头张望。回到十一连,一身大汗。 一年后,我也到了团部,先是在后勤处,后来到干部股,再后来到了宣传股,跟保卫股同属政治处,我跟胖子都在一个大部门工作,也算同事了。 但是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说话,见面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他总是面色严肃,跟王旭林几乎形影不离。王旭林比他和善多了,有时有个笑脸,打个招呼,但胖子的脸总是绷着。我有点怵他,但也不愿意巴结他。 他年岁大,来机关早,从事的又是专政部门工作,整天和阶级敌人打交道,带有保密性质。他们那个部门先是制造一起冤假错案,然后再去绞尽脑汁妥善摆平冤假错案,所以办公室总是关着门,嘀嘀咕咕地悄声研究事情,显得很神秘。我们宣传股就完全不一样了,常常嘻嘻哈哈,大声说笑,有时惹得隔壁李主任不高兴,就打开门朝我们屋子里望一眼,什么话也不说,但那意思都明明白白挂在脸上:这是办公室,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过杠了!我们就彼此会心一笑,敛声静气。 我想,许春青大概也看不惯我们嘻嘻哈哈不大正经的样子。他们才是干正经事的!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的关系才有了转机。 年春夏,北京重新出版了四大古典名著,在八一制片厂的同学齐晓明,给我寄来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在团部机关是头一份。老胖子来向我借书看。我心想,你也有求我的时候呀。 后来,我们有时聊聊书,有时聊聊古诗词,来往就多了起来。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当时正在修一条由团部经过关门嘴子通往饶河的公路,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走,聊着聊着,就聊到政治处的事情,我说了许多对于李主任的意见。后来许春青说,他就是从那一次起,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在那之前,他认为我在李主任眼睛里比较“红”。 很久以后,李炳华在我面前表示了对于李主任的非议,也是从那时起,我改变了对炳华的看法,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他是李主任眼里头号大红人。 渐渐地,我对胖子不仅有了好感,而且产生一种很强的信任感,把他看作老大哥。 我在火车上认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都把胖子看作老大哥? 我想出四条理由,第一,他真诚可靠,让人信赖。第二,他嘴严,能替人保守秘密。第三,他能给人出主意,想办法。第四,他慷慨大方,乐于助人。 年春节过后,我回哈尔滨治疗肺结核。 医院在王岗,只有一趟公交车,车少,间隔时间又长,很不好坐。政法干校门前有一站,一天早晨我去等车,忽然发现附近有个摊子在卖元宵。那年头元宵是稀罕物,我从下乡之后就没见过,所以喜出望外,买了一纸袋。一会儿,汽车来了,我穿着皮大衣,手里还抱着元宵,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车。汽车上人挨着人,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忽然我听到车下有孩子在喊:“谁的元宵,谁的元宵?三分钱一个呢,真有钱!”这时我才发现,包元宵的纸袋子已经破了。但我已经顾不得元宵了,只是庆幸终于挤上了汽车。 我把这段经历写给胖子,他回信说,“看到你信中谈到撒元宵的情况,不禁使我哑然失笑,你那狼狈相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下午组织生活休息时,我把你这段撒元宵读给大家听了,当然是哄堂大笑。” 年秋天,胖子回家探亲,来医院看我。 我们两人一起上街,去道里。在公交车上,售票员查票,我冲她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月票!”胖子买了一张票。下了车,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你还买月票了?” “没有,我没票。”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撒谎呀!” 我若无其事:“我跟住院的病友出去,他们谁也不买票,都说有月票,就我一个人买票。一问,他们都没票,还笑话我。后来我也不买了。” “售票员不查你们呀?” “不查,从来没查过。” 胖子用惊喜的眼光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行呀!练出来了!真要刮目相看了!” 我们进了哈一百,胖子说:刚才从你旁边过去那个人是咱们团的。 我转着脖子四下看,找不见一个熟人。胖子说,就你那眼神,早过去了! 我说,你行啊!练出来了! 他得意地说:咱们是干什么的! 马路对面是新华书店。他买了一本郭沫若手书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大十六开,文物出版社出版,黄色的封面上,画着几朵淡淡的梅花。他说,这书好! 我也买了一本,至今还还珍藏着,几次搬家清理图书都没有扔掉。 那期间,王增如也回北京探亲。我有了与她处对象的想法,和胖子说了,胖子很赞同,说,你约她上哈尔滨来一趟呀! 恰好,老父亲托外贸部的一位老乡,给我买了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新药,利福平,意大利出产的。如今已经是常用药品,但那时国内还没生产,医院也没用过,红色的胶囊,一粒一块一毛七分,每天空腹吃四粒,真够贵的。我就给王增如写信,委托她路过哈尔滨时停一下,给我把药捎来。 她是热心人,自然不会推辞,就来了。此前,胖子还写信托王增如给他妹妹许秀英买条裤子,信里说:“我有个妹妹,唯一的宝贝妹妹,我下乡几年来,家里大部分事情全靠她一人,甚至连我的穿用都是她给我办的,我深感有这样一个妹妹而自豪。她说要买条较好的裤子,但托人一直没买到,看来这是应该我办了。”王增如买了一条墨绿色的确良裤子,漂亮的许秀英十分满意。 我们在许春青家里见了两次面。但见面时彼此都有些误会,以为对方无诚意,算了!后来,又经胖子和吴燕平从中调解解释,终结百年之好。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为了保守秘密,我写给她的信件,都是寄许春青转。开始是夹在胖子信中,后来渐渐感觉不方便,毕竟是情书,就约定:信封上写“许春青收”的,是给胖子的,写“许春青转收”的,是给王增如的。再后来,只要是我的信,老胖子看也不看,一律交由王增如拆封,如是给他的,再由王增如转给他。团部邮局高旭东等几个小嘎子,都是胖子的铁杆,有时胖子外出,他们就把胖子的信件收好,等他回来直接交给他,王增如着急看信,去要,他们也不给。 由于有胖子这个可靠的秘密交通员,他的嘴又极严,所以我和王增如的事情密不透风,团里谁都不知道。后来,大白天下之后,张景龙政委十分不满意地说:”行啊,向东,你们两个的事连我都不告诉,还瞒着我!“ 年8月末,我们旅行结婚,在哈尔滨我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饭,算是家人的婚宴。一张小小的圆桌,姐姐姐夫炒了几个菜,除了家里人,只请了赵景惠叔叔和胖子两个人。这顿饭,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 在哈尔滨养病期间,我常上胖子家去,民安南头道街89号,这个地址我至今清楚记得,我从水利设计院,溜溜达达走二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种着菜,养着鸡,菜也长得好,鸡也养得好。操持家务的,是胖子的母亲,她是个干事麻利待人热心的老太太,对我很好,总留我吃饭,我在那个小院子里总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情。老太太常常叹着气说:“俺们春青,都二十八了!还没个对象呢,可怎么整?”她把俺,读作“nan”,上声。我说,他二十七周岁。她说,虚岁可不二十八了呗! 他们兄弟姊妹四个,许春青长的最像她母亲,脾气秉性也最像她母亲。 年春天,胖子考入哈尔滨师范学校,终于回城了。那时我已经在佳木斯广播电台工作了两年,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里。 我一直觉得,胖子天生是当干部的料,他具备一个合格领导干部的一切素质。 毕业后,他分到了市教育局办公室,好像还是个科长之类(后来似乎爬到副主任的位置),总之负点责任。我为了买火车票,曾经去过一次他们单位。我感觉,在市教育局那一段,充分显示出胖子的才能。办公室的工作,事无巨细,头绪繁多,但他游刃有余,不慌不忙,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同事关系也很好,上上下下都比较协调。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许春青,我想到的是“风华正茂”。 胖子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我为他高兴。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去一个下属单位。不知道是为了提拔他呢,还是被排挤了呢?我没有问过他。但是我想,胖子既无背景又无靠山,又不善阿谀之术,教育局办公室那样的肥差,不能长久立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胖子人品好,善于管理,责任心强,又很会与人打交道,挪动了几个地方,都干得很出色。在悼念仪式上,原哈尔滨师范学校老校长的悼词中,给予他公正的评价。 但是他病了。我一直觉得他的病源于他的胖。 年还是年,夏天,他来北京出差,在我家住了两个晚上。夜里,他的呼噜打得山响。我睡不着,就研究他的呼噜。他吸入一口气,有个停顿,再呼出来,有时一吸一呼之间停顿的时间很长,半天没有动静,我很害怕他憋死,就用手推醒他。他说,没事,老这样。 年代末,一年冬天,大嫂陪他来北京看病,医院那一带的一个旅馆里。一天下了班,我和王增如去看他们,找了一家饭馆吃饭,大嫂半开玩笑地说,哎呀,你们来了,我才能吃顿正经饭,这老胖子可节省了,净对付我!王增如说,大嫂,今天我请客,你想吃啥咱们就点啥!吃完了,王增如又说,这个饭馆不好,咱们再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好好吃一顿!过了两天,我们做东,在和平门烤鸭店,约了几个战友聚餐,有翟平吴燕平,有王志群罗海鸥,有蒋继先葛保国两口子,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一个姓谢的青年。郭玉锁也来了,从打年到北京,我头一次见到她,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她,几年后老郑来北京,打电话约她,她也没来。那顿饭吃得好,气氛也好,大家都很开心,是一次欢快的聚会。我记忆中,那是老胖子最后一次来北京。或者更准确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北京接待他。 年春末夏初,我去哈尔滨,给老父亲过八十大寿。在道里一家饭店摆了两桌。胖子和大嫂都来了,还坐在主桌上。我父亲也认识他,对他印象很好。 大约是在年夏天,老胖子来电话,说要“回饶河农场看看,咱一起去呀?”我自然高兴。那一行,有阎永杰、王云凤、王千、小韩等,火车上,大家说说笑笑很热闹。王千带的食品最多,她的话也最多,我和胖子、大嫂,就嗑着她的瓜子,吃着她的糖果,听她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翻腾那些芝麻和谷子。王千真是个十分可爱的好人,回到哈尔滨,又在一家档次较高的饭店里宴请大家,我们认识了她家里那位脾气性格好到极致的项先生。那个晚上,说话最多的是黄瑞升,他不停地说,不停地喝,抢了王千的风头。 饶河农场招待所,是一栋刚刚完工的新楼房,设施不完善,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夜里也没有电灯。男生住一起,女生住一起,大嫂嘱咐我说,你关照胖子点,他夜里要上厕所。 夜里,我听见胖子起来了,就问,上厕所啊?他说,嗯!我又问:我陪你去呀?他说,黑灯瞎火的,拉倒吧,我就在屋里解决算了。他找出个脸盆,哗哗地就解决了,然后上床,一会就响起鼾声。 我睡不着了,总觉得屋里有股子臊味,又懒得起来,思想斗争了半天,还是不行,终于下地,端起脸盆,拿到卫生间里倒掉了。 我们去饶河县城看望老郑和胡会计,住他们家里,也是男生(老郑、胖子和我)一个屋,女生(胡会计、大嫂和郑晓春)一个屋。老郑让我和胖子睡床上,他睡地铺,我说,我可不挨着老胖子,他打呼噜!最后,我和老郑都睡地铺,老胖子一个人睡一张大床。还好,那天他的呼噜不是很响。 有一年,王增如去哈尔滨办事,委托胖子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旅社给订个房间。那里是丁玲在年和年曾经两次入住,并且在《风雪人间》中写到过的地方,王增如很想看看,并感受一下。 她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老胖子一家三口去接站,直接送去马迭尔,并在著名的华梅西餐厅为她接风。回来后王增如十分得意地告诉我,我妒忌地说,我去过那么多次,老胖子一次也没接过我。 今年9月30号,国庆的前一天,王增如在单位值班,给胖子打了个长途电话。胖子第一句话就是:真难得呀! 王增如平时较忙,很少和他联系。 王增如说,你不抽烟不喝酒,怎么得这么个病。他说,就是在兵团时太能吃了。 那次通话时间较长,王增如感觉,胖子的心态很平和,但说话不太利索。回来跟我说了,我说,那是脑血栓的后遗症。 他对自己的病,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我从来没听他悲观过,抱怨过,甚至连个悲观和抱怨的表情也不曾见过。以他的精明,对于自己的病情,内心肯定一清二楚,但他泰然对之,不愿因此影响了家人和战友的心情。在对待疾病,对待生死的态度上,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在和谐号火车上,我接到靳立明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问我带的钱够不够,要我代他和邱柏生对胖子的家属“表示表示”。我问拿多少,他说小邱要拿一千,他也想拿那个数。我说,柏生还在岗位上,你退休了,就少拿点,减半吧!他说你看着办吧。接着是于夜广的电话,问我几时到站,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和阎永杰约好了,到师大安顿好之后,咱们一起去胖子家看看。 入住师大“贵宾楼”,我把我们的、立明的、柏生的、我姐姐的钱,给宝宝的钱和给大嫂的钱,分别装在信封里,就与夜子、永杰碰头,一起去了胖子家。 胖子家里设了简易的灵堂,我本来想,应该在胖子的遗像前鞠个躬,但是屋子里有外人在,我和胖子对视了一下,终于没有弯下腰去。我想,胖子和大嫂都会原谅我的,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不懂礼数。看到大嫂和宝宝都还平静,我略觉心安。大嫂向我讲述了胖子住院直至去世的详细经过。疾病严重侵害了他的多个内脏器官,现代医学救不了他了。我想,好在他死亡的过程不算长,他自己少遭罪,也让家人少遭罪。他向来都是替别人着想的。 从胖子家出来,我们三个找了家饭馆,一起忆起胖子的种种。夜子和永杰说起,10月6号,宝宝结婚的前两天,他们俩一起去看胖子,那天胖子情绪很好,话也很多,一直聊了很久,聊到许多事许多人,他的胃口也很好,还吃了他喜欢的肥肉。我说,那大概是胖子最后一次倾心交谈了,你们俩真有福气。夜子说,哈尔滨这些知青,胖子是个头,大事小情,总要找他商量。永杰说,一九九几年来了一拨上海知青,回饶河,到了哈尔滨,咱们得招待呀,安排住旅馆,不能让人家花钱啊,胖子一下就拿出一千块给垫上了,那时候一千块可不是个小数。这些年,只要有知青来,不管是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回饶河都得从哈尔滨路过,第一顿饭要是没人请客,都是胖子安排,他可大方了!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那天很冷,我穿上永杰给拿来的呢子外套和厚袜子,还冻得打哆嗦。22团的战友们又聚在一起了。来的人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多,许多人都没有通知到,后来姚桂荣就埋怨说,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是老胖子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召集我们了。而他自己,却穿戴整齐,两眼紧闭,安卧在玻璃棺中。战友们依次从他身边走过,向他鞠躬,与他告别。 老胖子看见了女儿的出嫁,可以安心地走了。他没有白挨那救不了命的残忍一刀,也免受了许多痛苦。 丧事的最后一项是吃饭。我们又围坐在圆桌旁,叙友情,发感慨,频频举杯,其间不时开个玩笑。我一边笑着一边又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开玩笑,是否对于死者的不恭呢? 我又想,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这一定是老胖子最大的心愿,看见亲人和朋友们高兴,他心里一定也是高兴的。 老胖子走了,我少了一个思念的人,多了一个怀念的人。 我和胖子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22团的战友,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我们之间看人看事,观点十分接近,在他面前,我的心胸彻底敞开,一点秘密也没有,什么都毫不隐瞒,而他总是眯着眼,微张着嘴,脸上浮现出一种慈祥的微笑,听我把话讲完。我知道他喜欢我,虽然他的朋友很多,但是,我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朋友。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 ○ 时光荏苒峥嵘岁月 李向东赞赏 长按北京白癜风的价格是多少老牌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饶河县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系列我们的老大哥
时间:2018-11-2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6月份,117位院长主任落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