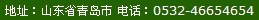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内容提要:戏曲被分为多个“剧种”,但“剧种”这一区分地方戏的称谓并不是历史形成的。地名取代声腔成为地方戏的分类标准与命名方式,始于晚清和民间年间的大众媒体,马彦祥等人有关地方戏的研究强化了以地域命名剧种的现象。在“戏改”过程中,剧种的命名才最终完成,但是由于行政的力量在其中起支配作用,因而留下许多遗憾。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戏剧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多元的形态。“剧种”是当下人们用以区分戏曲内部形态差异的主要范畴,按“剧种”的区分,通常认为戏曲可以区分为多个剧种。戏曲之所以被区分为如此之多的“剧种”,实由于“剧种”这个20世纪才出现的戏曲分类学术语被普遍运用,而“剧种”这一称谓是何时出现以及如何出现的,迄今我们还不能从任何研究文献中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刘文峰先生在《关于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中认为,“剧种”这种称谓被普遍运用,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戏班登记时,登记表中设了‘剧种’这样一个栏目,于是各地戏班给自己演唱的戏曲起名为‘某某剧’”,这一观点应该援引自我在戏曲档案中发现当年的“剧团登记表”时所产生的误解。我提出这一看法时,主旨是为了追溯“剧种”一词的出现与剧团国家化的关系,因而对“剧种”的称谓来源未做细致考察。实际上用“剧种”作为各地流行的地方戏的称谓,要远远早于剧团登记。举例来说,年初创办的《新戏曲》杂志,从一开始就是用剧种来称呼地方戏的,这一点已经和今天没有任何区别;而上海市举办的戏曲改进运动春节演唱竞赛的获奖名单上,也明确标示着京剧、越剧、绍兴大班、沪剧、江淮戏、维扬戏、甬剧、常锡戏、滑稽剧等,虽然“江淮戏”等具体名称与现行通称有异,但其中体现的剧种意识已经非常之清晰。从年8月开始,《新戏曲》开辟专门的栏目介绍地方戏,从10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五期开始,特别给这个栏目加上了“各地剧种介绍”的名称。田汉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代表文化部作的报告《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提及各地包括“地方大戏”、“民间小戏”在内的地方戏后,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各地戏改工作以对于各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对象”。这些材料都充分说明,“剧种”这个范畴术语,年左右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和文化部门正式文件里,已经被普遍使用。而大规模的剧团登记,要迟至年才开始。文化部在年1月29日发布了《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开始全面部署并强化全国性的剧团登记和整编,随后于5月13日颁发《文化部关于全国剧团整编工作的几项通知》、12月12日发布《文化部关于私营剧团登记和奖励工作的指示》,次年10月14日发布《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的登记管理工作的指示》,年6月17日下发《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的补充通知》。在此之前,或已有部分省份提前开展的剧团登记工作,但不会早于年。所以,剧团登记表上出现“剧种”这一栏目,固然对相当多地区的艺人命名自己所演唱的戏曲样式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前,“剧种”一词在政府文化部门的使用已经很普遍,登记表的设计只能是其结果,而非其原因。 总之,“剧种”作为一种区分各地方戏曲的称谓方式,它的出现以及流行的过程并不单纯。我们只知道它并非戏曲诞生以来就有的词汇,如果能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用语的来源做一番考原求证的工作,或许能够深化我们对戏曲的历史与发展演进的认识。 戏曲历史悠久,分类及命名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南戏、北曲是基于所诞生区域的区分,杂剧、传奇是基于文本形态的区分,雅部、花部是基于美学取向的区分,但相对于丰富复杂的戏曲,这些区分方法终究过于笼统。而随着戏曲在各地广泛传播,音乐与方言语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配的关系逐渐上升,最终导致各地方戏曲在形态与性状上呈现出诸多的差异,戏曲的地方化特征才得以充分显现。正因为这些地方特征多半与地方语音的腔调相关,所以基于腔调区分和命名各地的地方戏曲,就逐渐成为新的习惯,祝允明《猥谈》和徐渭《南词叙录》等早期文献里,这种区分和命名方式就已出现。 因此,从戏曲开始呈现出地方差异的明初时期起,各地方戏曲就是主要以腔调为分类依据的,明代的“四大声腔”和清代文献中所称的高腔、梆子、乱弹等,都是在强调彼此间声腔的差异(其中“乱弹”之名,看似与声腔无关,但是它所指称的也是音乐的性状特征,且因音乐上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可辨识性)。昆曲或曰昆腔就是最好的例子,“昆”虽然本为地名,但因为它在全国各地得到最广泛的流传,与它的原生地昆山的地方文化的归属关系早就模糊了,“昆”作为地名的意义远不如它作为声腔的意义那么重要,对“昆”的辨识,主要是对音乐性状和声韵的辨识而非其他。 在戏曲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梆子、乱弹等民间性很强的声腔广泛传播,一方面戏曲的音乐与地方的方言之腔调相表里的特征日益重要,这些俗文化范畴内的声腔,又不像昆曲那样有严格规范,所以同一声腔在不同地区难免出现其或大或小的流变。高腔、梆子和乱弹的流传区域都十分广泛,在漫长的时间内,在不同地区均逐渐出现、形成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和不同的风格。同样都是高腔、梆子或乱弹,相互间的差异可以很大,因而加剧了戏曲内部构成的复杂化,并且经常出现同名异腔的现象。所以,习惯上人们也会在声腔的基础上冠以地名,用以区分各地的地方戏曲,如“梆子”有上党梆子、山陕梆子等,高腔、乱弹无不如此。至于花灯、采茶、花鼓、道情、秧歌等小戏,其音乐表达原本就相对简单,各地相类似的表演更不可能太受其内在的规定性的制约,也就更加容易产生地域性的差异。这既是地方戏出现的原因,同时也正是戏曲史上出现以地域名称为地方戏命名的缘由。当然,戏曲声腔内在关系复杂,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是业内还是社会各界,包括文人学者,历史上从未有人按声腔为戏曲的地方戏做过全面而精细的分类与命名,这也是事实。 总之,用声腔为地方戏曲命名的方法,其出现与流行可以远追至明初,而用地域为地方戏曲命名的方法,或者在声腔前面冠以地名的命名方法,在清代已经多有出现。这些称谓都是自然形成的,或能得到伶人和各地戏曲观众认可,但多无规范可言。所以我们看清代的文献,例如“乱弹”这样的称谓,所指称的对象之错综复杂,莫衷一是。 二、地方戏命名方式的新变化 晚清时,有关地方戏的命名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剧称谓的变化。 晚清时,京剧业内人士多自称为“皮黄”。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它在声腔上具备以西皮、二黄为主的音乐属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地方戏的最重要特征。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京戏”和“京剧”之名,在媒体上很早就大量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申报》等大众媒体上,“京剧”或“京戏”的称谓被大量地交替使用,在新兴的杂志类媒体上,这种称谓非常多见。随手摘抄几条:年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京剧”的称谓,年创办的《游戏杂志》,几乎每期都设有“京剧”专栏,介绍京剧的重要剧目或伶人;年出版的《通学报》第二期介绍社会上的冤事,称“京戏有《九件衣》一出”,年《滑稽杂志》第一期刊有诗丐撰写的《京戏名对》,年出版的《俳优杂志》第一期刊有《京戏术语》一文(不署著者),等等;清末上海剧评家郑正秋写的文章里,“京剧”一词也很常见。而使用“皮黄”者,越来越限于业内人士或所谓“行家”。 民国中期,仿照“京戏”、“京剧”的称谓方法,用地名冠以“戏”或“剧”的方式为地方戏曲命名,有逐渐普及的迹象。如“粤剧”的称谓,可查到年《益世杂志》上的剧本《书生忧国》,前面署有“粤剧碎锦”的题名;年《游戏世界》杂志上刊登过刘豁公和人合写的《粤剧杂谈》,如果我们再翻检同时代的其他报刊,不难找到很多文章使用“粤剧”这一名称。至迟到20世纪的20年代末,这个称谓在各报刊上已经非常通用。再看其他地区的地方戏曲,年第10期《戏剧月刊》载有署名夏晓东所著《汉剧现状》,年《剧学月刊》连载杨铎著的《汉剧十门脚色及各项伶工》,年出版的《蹦蹦戏考》的印行者署名为“评剧研究社”,年《十日戏剧》杂志连载邹少和著的《豫剧考略》,这些作者使用的剧种名称,都已经与今人无异。除了秦腔偶有人称之为“秦剧”,并未普及之外,“川剧”、“粤剧”等名称,都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报刊中的常用词汇,而“豫剧”、“越剧”之类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基本上已经为大众媒体所经常使用。无论是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还是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各地方戏曲的名称,都逐渐开始流行后来最多见的“地名+剧”模式的称谓。 当然,在民国中后期,虽然在地方戏曲中冠以地名的现象急剧增加,然而“地名+剧”的命名方式,仍然只是地方戏曲若干种命名方式中之一种。以广西地区清代开始流行的弹腔为例,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桂戏”的称呼,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西南剧展”并为之创作新剧目时用的是“桂剧”,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桂戏”和“桂剧”两种称呼仍然同时并存,在《戏曲报》第三卷第七期发表的方非的长篇介绍文章《关于桂戏》,题目中用的就是“桂戏”而非“桂剧”。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地方戏曲的称谓的形成,发生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从“内命名”向“外命名”转变的过程。其中关键性的变化,就是地方戏的命名原则,从其艺术属性的界定,逐渐转为与其艺术属性关系不大(至少从表面上看)的地域化的界定。地方戏的分类方法从内命名向外命名的转变的结果是,原来地方戏最核心的辨识标志是声腔之不同,此时却变为地域代之以成为其主要的辨识标志。这一变化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从内命名向外命名的变化,还因为导致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辨识标志的替换,其动力显然源于梨园行外,它的命名主体是戏剧界之外,尤其是大众媒体,又尤其是异地的大众媒体。简单地说,命名主体从内行变成了外行,从本地人变成了外地人。正因为此,相对于地方戏的声腔音乐而言,地名显然是更容易为大众(尤其是异地的)媒体的编辑、记者和读者们认知把握,也更容易辨识的元素。面对更多元的观众,冠以地名是更容易普及的称呼;基于更大范围的传播,地名作为辨识指标的作用也更显著。因而,它放弃了对地方戏曲的形态与性状、尤其是在艺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音乐和声腔的特点的界定,换取的是更广阔的地域的更多人、尤其是“外行”的接纳。其实从几个细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与命名主体的关系。“京剧”一词首先出现在上海而不是北京,年后,《申报》上“京剧”和“京戏”的名称大量出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天津的《大公报》上同样有大量京剧消息,却迟迟看不到这样的称呼;民国时期,在戏剧类专业杂志上,“皮黄”这个称谓比起一般的大众媒体而言更为多见,相对于后者通常更多使用京剧、京戏(或北京改称“北平”之后更通用的“平剧”)这些词汇,当然是由于戏剧专业期刊上撰文的作者和读者中更多剧界人士,他们对声腔更为敏感,也不愿意追随大众媒体,使用虽然通俗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声腔音乐之特征的“地名+剧”这样的称谓。 尽管从晚清到民国,在各地方戏的称谓上冠以地名逐渐成为通例,但这种命名方法毕竟有无法解决的困难。问题在于地方戏曲的流播以声腔为基础,而声腔不仅仅意味着音乐旋律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文本的差异,进而意味着剧目的差异,甚至导致表演手法的差异。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每种声腔都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代表性剧目,形成了某些特有的表演技巧与手法,自成系统。而声腔的流传区域更不可能完全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不同声腔流传的地区往往犬牙交错,且同一地区往往流传着不同声腔。以西南地区为例,从民国初年起,这一带流传的地方戏通称为“川剧”,但它实际包含了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等几大声腔系统,还保留有部分昆曲剧目。虽然民初就有人仿照“五族共和”之意提倡“五腔共和”,普通民众也早就习惯于使用“川剧”或“川戏”的统称,但是具体到那些重要的保留剧目,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艺人们仍一直坚持要明确界定各自所属的声腔。对不熟悉川剧的普通观众,或者对那些不了解川剧声腔的复杂性的学者来说,川剧就是川剧,然而对川剧艺人和资深的川剧观众而言,不同的声腔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态,是无法满足于只使用笼统的“川剧”这一个概念描述的。 川剧遇到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如前所述,声腔的流布与方言区高度相关,四川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因属于同一个方言区,所以三省都是川剧流行区域。但云南另外还有滇剧,贵州另外还有黔剧,为什么云贵地区流传的多声腔的川剧要叫“川剧”,而不是和那里的地方戏并称为“滇剧”和“黔剧”?川剧只不过是用地域命名剧种时遇上麻烦的中国无数地方戏的代表。声腔的差异与方言语音的差异相关,而行政区域的划分与方言区不可能完全一致,基于声腔命名剧种和基于行政区域命名剧种,一定会出现矛盾。这就是漠视声腔等内在的艺术特质的差异,而简单化地依赖分布区域命名地方戏曲的方法的局限。但是,在晚清民国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之下出现的地方戏新的命名方法逐渐普及之时,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缺失将对戏曲的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三、“剧种”与地方戏研究 对地方戏曲的重视与认知,必然引向对各地的戏曲之内在差异的认知。大约民国中期,学术界对戏曲的北京治白癜风的最好医院白癜风医院成都哪家好
|
时间:2017-10-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黑龙江省艰苦边远地区县公务员公告已出,招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