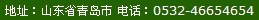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他们是我们饶河农场的建设者。这片土地上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生命轨迹从此改变。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 马号的故事 董勤朴,哈尔滨第五中学高中二年。年10月16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二团五连。历任农工,后勤排长,连副指导员。年离开兵团返哈。 连里的马号坐落在村西北角,马棚是一趟长长的、有些变了形的泥草房。棚里拴着二十多匹膘肥体壮的大马。在下乡的岁月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些马打交道。马棚南头的饲料间有一铺炕,我与饲养员老张头共用,他炕头我炕稍。饲料间既是我的寝室,又是马号的会议室。我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和马号密不可分,粗看起来,我每天似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细想想,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每天又都有每天的故亊。 遛马 遛马这活,好汉不愿干,赖汉干不了。开春后,马号骟了一匹儿马,我安排徐金旺负责遛马。徐金旺三十多岁,身体不好,瘦削蜡黄的小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眼睛不大,看人总是直勾勾地,似乎是受过惊吓或刺激。我让他遛马其实是想照顾他。 骟马时,兽医老王有交代,这马必须每天遛,否则会粘连发炎,那事可就麻烦了。我把这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徐金旺。要求他每天坚持遛,不能偷懒!徐金旺瞪着小眼晴,连连点头称是,末了还向毛主席做了保证。 开头两天一切顺利,徐金旺倒背双手,牵着好似驯顺的黑马,嘴里哼着不知什么歌,在野径村路上悠哉游哉地遛着马,旁人都投以羡慕的目光。 ?可一周后,风云突变。那天,徐金旺变貌变色地对我嚷道:“排长!我……我,我不能干了!这野马总跑!”他直瞪着恐惧的小眼晴说,“我抓它,它踢我,谁抓踢谁!差……差点把小孩踢了!”刚骟的马七天后确实不好遛,因为刀口不疼了,就总想调皮撒欢。但就得坚持遛,否则这匹马就毁了。我安慰他说:“我知道不好遛,没关系,咱俩一起遛!”我想,牵着不好遛,那就骑着遛,不怕它跑到天边去!我背上铝制的行军水壶,带上干粮,做好了全天遛马的准备。 “来,金旺,你牵着马我来骑。”我把马缰绳递给徐金旺,随后,不动声色地贴近马前肩畔部位,猛然跳上马背。上了马,刚想调整一下姿势,哪知那马长嘶一声,前腿一抬,马身高高立起,我急忙抓住马鬃,两腿紧紧夹住马腹。不料,马前腿刚放下,后腿立即高高跳起,把我直接掀到马头。更可恶的是,它前腿又一跪,把我利落地甩到马下。我气极了,趁马还没站起来,一骗腿又重新骑在马上。徐金旺見状,冲我伸出大拇指,大呼小叫地赞道:“厉害!厉害!”我担心马往马棚跑,于是让徐金旺牵着马朝四号地走去。四号地刚翻过,地很松软,多调皮的马也跑不起来,不怕它不听话。 ?我骑在马上,视野立刻开阔,五连全貌尽收眼底。村落虽不大,但疆域无边。初春大地色彩单纯而大气,黑色地块是刚刚翻过的,嫩绿色地块是正在生长的麦田,那灰黑色地块似乎是去年秋翻地的颜色。远处可見几台拖拉机正在作业,头上冒着朵朵白烟。近处几栋红砖白瓦的平房刚建成不久,马号前还有一堆堆用于基建的石头。这些石头洁白耀眼,棱角锐利,堆挤在一起,象是雪山的微缩景观。 ?看到这景色,马玉涛的歌声在耳边迴响:馬儿啊,你慢些走哎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夠,噢……噢……噢……没等“噢”完,儿马子猛地挣脱了徐金旺,掉头朝马号奔去。事发突然,马速又快,我不得不手抓马鬃,伏下身子,任两耳风声呼呼,前方景物扑面而来。突然,儿马开始跳跃前进。原来,马慌不择路,跑进了石头堆。骑着光背马,又无缰绳在手我只好死命抓住马鬃,在扭来跳去的马身上保持平衡。如果在尖角锐利的石堆上,从疾驰的马上跳下,后果可想而知,不是腿断臂折,就是头破血流。我只好待出了这个石头阵再说。 ?一阵颠簸,总算出了石头阵。看到了宽敞平整的马号大院,我長舒一口气,准备相机跳马。没想到,那马并不减速,直奔马棚小门而去!我大吃一惊,若闯进小门,我双腿必被别断!没有选择,这马跳也得跳,不跳也得跳!我瞪大双眼,大喝一声“吁!”翻身跳下马背,那马也出人意料地立即原地不动,这时离马棚小门只几步之路! ?由于紧张,我抓马鬃的手已僵硬,不能伸屈。忽然,马号的饲养员老张头发現我手里攥着两大把马鬃,而黑马的马鬃处有两个明显的缺口。不用说,是我把马鬃当成救命稻草,从马身上硬生生地拔了下来!也就是说,在危險时刻,我几乎什么都没抓住,抓住的只是一个希望,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希望! ?相信的力量有多强大?因为我相信我抓住的是实实在在的马鬃,所以在石头阵上那一刻,尽管马又蹦又跳,扭来扭去,我也数度几乎从马上滚下,但我却一直保持着“动平衡”!设想一下,当时如果有人告我以实情,说我没抓住任何东西,那我可能会立即落马,我的命运就会因此而改写! ?这时,马号前已聚集了许多人,人们议论着、感叹着刚发生的事情。我摘下落马时摔扁的行军壶,把马交给老张头,自顾自地走开,心里想:我算好汉还是赖汉呢? 溜缰 北方初春的早晨依然很冷。窗前一阵烏鸦聒噪,不远处几声犬吠,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老张头早已起来,他喂饱饮足了马,然后把它们逐个从马棚牵出,拴在门前大院的马桩上。马棚四门大开,光线乘机普照马棚的每个角落,窝憋了一宿的糞臭气、尿臊味也不失时机地溜出飘散。村子里,残雪消融,燕雀争鸣。家家户户的炊烟在霜雾中袅袅升起。马号大院里,晨阳斜照,长影在地。马儿们愉快地活动着四肢,老张头乐呵呵地忙活着,马号的清晨一派祥和景象。 ?忽然,老张头气急败坏地闯入饲料间,大呼小叫:“不能干了!干不了啦!”我正洗漱,忙问:“出啥事了?”老张头指着正在院里撒欢的黑儿马嚷道:“这家伙又溜缰了!总溜缰!我不干了!”溜缰,就是马挣脱缰绳。老职工讲,溜缰的后果就是这匹马会横踢马槽,会和院里拴在马桩上的马挨个比拼。轻者破坏马棚秩序,导致多匹马挣脱束缚出現混战局面;重则这马又踢又咬,难保马不受伤误工。我没多想,直冲那匹脱缰马跑去,老张头随后跟出,嘴里喊着:“当心!当心!” ?那马正玩得性起,看我们过来捉它,便尥着蹶子,拖着長長的缰绳在院里狂奔起来。这时,马号的老职工们陆续来上工了,見此情景,都张开双臂自动圍成一个扇形,老张头带头“呀……呀……”地喊着,大伙也跟着高声吆喝。那马见大势不妙,急忙转蹄朝马棚两开大门跑去。太好了!我迅速跟进。老张头喘着粗气也朝马棚跑过来。马棚里,只見那马拧着头,不情愿地站在角落处,四蹄余兴未尽地跺着地。我接过老张头递来的爬犁杆,把杆横卡在马槽上,堵住了马的出路。待马稍一安静,我猛然出手欲抓马笼头,哪知那马突然长嘶一声,四蹄腾空,飞身从我头上掠过!粗粗的爬犁杆也随着飞起落下,重重砸在我身上。我两眼一黑,向后便倒。倒在满是马糞的硬地上,可感觉象倒在软软的棉花堆里……。 ?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現自己已经躺在饲料间的土炕上了,清扫马棚的肖姐和四、五个家属工围坐在我周围,急切地看着我的臉,站在后面的几个车老板则伸头探脑地看我的腿。我不知什么情况,忙问:“那马抓住了没有?”肖姐指了指窗外:“抓住了,拴在院子里。”我欠身一看,老张头正挥着大鞭教训着黑马。抽一鞭,骂一声,“我日你娘!叫你跑!”再抽一鞭,“我日你奶奶,叫你踢人!”又抽一鞭,“我日你祖宗……”“叭!叭!叭!” ?“别动别动!血还流着呢!”肖姐表情焦急痛苦地指着我的腿,大声叫着。我这才看到我左腿汩汩冒着血,血顺着小腿、鞋、鞋尖,流到炕上,再流到地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巨痛直袭全身!我膝盖部位已被血完全浸透。“排長,没事,郝医生马上就到,没事,啊。”肖姐她们安慰着我。郝医生是连卫生所的,记忆中是上海人,面善人和气。话音刚落,他背着诊疗箱气喘嘘嘘赶到。大家自动为他让出地方,他忙不迭地坐下,边开箱边说:“别急别急!我来看看,我来看看!”他拿出镊子、药棉,戴上口罩,准备清理查看伤口。在郝医生的指挥下,大家小心翼翼地帮我把伤腿的裤子脱掉。在血肉模糊中,近两寸长的伤口露出,深可見骨。“好险啊!拣了一条腿,正好伤在膝盖和小腿骨的骨缝中。”郝医生望着我,柔声说道:“没关系,止住血,缝上几针就会好的。”他给我打上麻药,穿针引线,准备缝合。我躺在炕上,望着屋顶,胡思乱想,尽力分散着注意力。苍蝇们闻到血腥味,成群结队,飞舞着,旋转着来到手术现场,要参与这一重大活动。郝医生边指挥众人轰苍蝇边做缝合手术。 ?猛然,一阵刺骨剧痛迫使我象油炸虾一样弓身坐了起来。“很痛吧?很痛的,很痛的。”郝医生抬眼看着我说:“可能是麻药打少了,打少了,忍着点忍着点,就好就好。”他边说边顺手将落在伤口上的苍蝇赶跑。然后,继续着针线活。 ?约摸半个时辰,手术完毕,郝医生擦着头上汗珠,指着我的腿说:“包札好了!千万别动、别打开,会感染的!好好休息吧,要静养,静养!”我望着被纱布包得粗大的膝盖,使劲点了点头,说:“谢谢郝医生,我就不送了!”郝医生理解地把手往下按了按,转身走了。 我独自躺在炕上,听着窗外车老板吆喝牲口的声音,家属工们叽叽嘎嘎的说笑声。只见老张头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粗着嗓子喊:“我把那匹儿马子狠狠教训了一顿,看它还敢不敢溜缰?”说着,蹲下身,往灶坑里续了续柴火,火突然旺了起来,他顺手把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扔进火里。 老张头是个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每天除了喂马,给马准备草料,便是躺在炕上呼呼补觉。“这马光惯着也不行,该打也得打。”他边嘟囔边试探着把那团黑东西扒拉出来。“死耗子?”我惊呼。“嘿嘿,好吃好吃。”他边说边认真地剝去老鼠被烧焦的皮毛,一团白嫩的,冒着热气的老鼠肉送到我跟前。“排长,吃点吧!这都是吃粮食的动物,一点儿也不脏。你流了那么多血,快补一补吧!”他真诚地说。我苦笑着摆了摆手,想起我早饭还没吃。真是想啥来啥,肖姐来了。她端着一大碗面条,里面还打了两个荷包蛋,香喷喷、热腾腾送到我面前。她推开了老张头,“去!去!一边去!谁吃你那玩意儿?恶心不?”老张头讪笑着退位了。“唉,咋整?你伤得这么重,你家又不在这儿……”肖姐看着我的伤腿说,神情有些戚然。我赶忙安慰她:“没事,肖姐,一点事都没有,过两天就好!” 过了两天,我的腿开始肿胀,伤口奇痒,全身发烧。郝医生过来看我时,说:“没事,伤口发痒是要长新肉,再观察覌察!”又过了两天,烧仍不退,腿已完全不能动了。郝医生也沉不住气了,说:“医院吧,医院!” 医院,医生打开脏兮兮的纱布,只见伤口已经化成了一个脓坑,里面积满黄乎乎的脓,臭气熏人。医生摇着头,说:“你体质真不错,若不然,悬哪!” 我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临出院时,我给母亲去了封信。“……好长时间没去信了,儿在这边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着!活蹦乱跳,妈放心吧,妈要多注意身体,有重活等我回去干……”可谁知道我何时能回家呢! 天快暖和时,我一瘸一拐回到了连队,回到了喧闹的马号。 董勤朴赞赏 长按中科白癜风医院践行公益事业北京看白癜风疗效好专科
|
当前位置: 饶河县 >饶河农场知青故事22马号的故事
时间:2018-8-2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管理局顾毅局长一行到饶河调研
- 下一篇文章: 建三江人民医院各科室介绍,寻医问诊不盲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