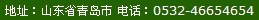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点击 胡瑞华原名胡水花,年出生于饶河支流昌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上。出生时,身量瘦小的她却有着一副亮得出奇的噪子。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女婴日后将会成为一代著名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幼年时的小水花从来就不会浪费上天赐给她的好噪子,整天依依呀呀地唱,有时也会和着爱拉胡琴的父亲的琴声唱上几句饶河调。不过,尽管外祖父家是赣剧世家,外祖父有事没事地也教小水花唱几段《三司会审》,但饱尝唱戏艰辛的长辈们,谁也没有想过让小水花继承他们的衣钵。或许是上天要把这个女孩子固执地塞给赣剧,不管家人怎样回避,小水花还是从村里一次请戏班演戏过后,萌发了强烈的要学演戏的欲望。 磨过了母亲出于对女儿疼爱的阻挠,丢下一句“演戏我也不会丢下弟弟妹妹不管”的承诺,年,小水花进入饶河戏班学戏,第二年又进入到刚成立的鄱阳县赣剧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 初到剧团,小水花非常刻苦。由于她学戏时已经15岁了,错过了最佳的学戏年龄,这意味着她要想唱出名堂,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每天清晨天不亮,她就会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县城的新桥附近,对着东湖喊噪子。那时东湖一带是乱坟岗,一般人很少到那里去,但憋着一股劲要唱好戏的小水花丝毫也不害怕,总是用她那嘹亮的噪子和百鸟对歌,随朝霞起舞。这一年的大年三十,她是在剧团里度过的,原因很简单:怕一回去家里就不让再出来了。 胡瑞华张星斗剧照 年,一场大洪水席卷了赣东北大地。这年的冬天,鄱阳、乐平、余干、万年等地的数万民工齐聚鄱阳县城,打响了水利冬修的大会战,修筑饶河联圩。当时,经历了几乎解散命运的剧团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紧张而又简单地筹备后,剧团最终恢复了正常的演出。第一场戏演下来,竟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巧的是,几天后,剧团驮梁旦奉命进省城汇报演出去了,剧团本来旦角演员就少,这下更是捉襟见肘了。情急之下,老师傅们决定把小水花推到前台。打炮戏是她向外祖父学的《三司会审》。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小水花,这回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了。她把心一横,一句“来至在都察院用目观望——”冲口而出,立刻在观众中炸了锅:哇,这噪子,能耕山呢。赣剧观众看戏看到兴味盎然处,不像京剧观众那么斯文,鼓掌叫好,而是一阵“咦呵呵——”,跟着就是打浪,掀起的人浪一阵高过一阵。小水花甫一登台,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紧跟着问题就来了,由于她学戏晚,根本就不会几出戏,可是观众却非点她不可。怎么办?总不能老是唱《三司会审》啊!情急之下,剧团的老演员每天晚上演完戏后,在冰冷的月光下给小水花说戏,现排现演。小水花在这种情形下,竟然表现出她过人的天分,硬是在一个月内连续上演了《七姐下凡》、《嫦娥奔月》、《白蛇传》等五六出大戏。观众们从此记住了一个叫胡水花的有着一条铁打的噪子的赣剧小花旦。等剧团驮梁旦从省城再回来时,观众已经非胡水花的戏不看了。就这样,小水花凭着一条天赋的好噪子一下子红遍了赣东北。 赣剧,特别是饶河调,虽然是南方戏,但却在表演和唱腔上有着北方戏的粗犷和高亢,因此,一直为男性观众所喜闻乐见。小水花的出现,为赣剧掀开了新的一页:一大批原先只钟情于越剧和采茶戏的女观众,纷纷加入到赣剧观众的队伍中来。这无疑得益于小水花那优美的唱腔和充满女性特有魅力的表演。四年后,她参加了江西省戏曲汇演,《一块手表》获表演奖。年6月,她把《三司会审》唱到了北京,使北京听众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二黄”故乡的皮黄。同年8月,她又上庐山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做献礼演出,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这之后,她为自己取艺名胡瑞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改名,这标志着她企望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有一次飞跃。之后的几十年舞台生涯中,她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为丰富赣剧的表演和声腔艺术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胡瑞华爱赣剧,也爱自己的观众,在她看来,赣剧是她的生命,舞台是她的天地,观众是她的上帝。为了赣剧,她付出过很多,甚至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因为生病期间她正在外地演出,耽误了治疗而夭折了。在每次演出中,如果剧中没有她的角色,她为了满足观众的愿望,总在演出前或结束后,应观众的要求加演清唱或折子戏。她的付出也赢得了观众的爱戴。她获得过党和政府授予她的许多荣誉,但她最在乎的却是由大众海选投票获得的“鄱阳县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光荣称号。 胡瑞华授徒仪式革故鼎新瑞英吐华更芬芳 文革十年,胡瑞华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蛰伏了一段时期。文革后期,她又被重新启用,改演京剧样板戏。这一段时期,她虽然远离了心爱的赣剧,但这段唱京剧的经历,却为她日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声腔艺术提供了帮助,京剧行腔吐字的讲究给了她很大的启示。 文革结束,年,在《十五贯》等一批传统戏恢复之前,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胡瑞华冒着风险一夜之间恢复了《装疯骂殿》,这小小的一出折子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一些老观众听到那久违的熟悉的声调,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从此,胡瑞华焕发了艺术的第二青春,她的“胡派”艺术也就是在这期间开始形成。 重上舞台的后的胡瑞华,仍然没有停止她前进的脚步。而促使她在这一期间加大步伐进一步锐意改革的却是观众一句话:“胡瑞华的噪子真好!”这看是一句赞扬的话语,在胡瑞华听来却是尖锐的批评:噪子好?只说我噪子好,不就是说我唱得不够好吗?生性要强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观众说她唱得好。如果说,以前胡瑞华的艺术革新是出于下意识的话,那这一阶段她则是主动迈开了改革的步子。早期景德镇电视台摄制经典赣剧《装疯骂殿》胡瑞华、石桂安、吴寅生主演 提到“胡派”唱腔,不能不提到《十五贯》中那段著名的“老拨子”。赣剧的老拨子(另外还有“上江调”也是如此)唱腔,使用唢呐伴奏,高亢激越,热烈奔放,观众很喜欢听,但是对演员的噪音条件要求却非常高,必须盖过唢呐,才能让人听清楚唱词和唱腔。当然,这对于天生一副好噪子的胡瑞华来说,似乎并不是难事,她的噪音好像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高音挡得住,每次演唱都是满弓满调,拿赣剧的行话来说就是很“吃板”。但胡瑞华不满于此。在率先恢复的传统大戏《十五贯》中,她扮演苏戌娟。在《起解》一场,有一段老拨子唱腔,胡瑞华觉得原来的唱法悲切有余,愤恨不足,于是,她大胆地吸收了赣剧男腔的老拨子的曲调和唱法,使得这段唱腔更加刚劲,更加高亢,也增大了演唱的难度。第一句导板“刀斧手喝一声我胆战心寒”,“手”和“寒”两个字均为开口音,对演唱者的噪音是个考验,一般人唱到这里,都要在后面加上闭口音的衬词“咦”,但胡瑞华一如既往地去掉了衬词,却唱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并且一改以往女腔柔韧的唱法,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音调上扬,宛如一根抛物线,显得刚劲挺拔又不失柔美,最后句“活捉瘟官架子阎罗殿前讨还血债还我命来”,把全段推向高潮,把苏戌娟对昏官酷吏的一腔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听得荡气回肠。这个唱段一经推出,立刻被广泛传唱,成为“胡派”唱腔形成的标志。而在《胭脂狱》中,同样有一段《双起解》,也唱老拨子,但胡瑞华却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刻画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又爱又恨的复杂心理。在赣剧《武家坡》中,王宝钏出寒窑时有一句西皮十八板“王宝钏出寒窑,低头打一瞧,只见一枚钱,用手来捡起,原来是半文钱,上街头,买不到半粒米,下街头,扯不到半根线,你笑我,夫妻团不得圆,我道你有眼无边沿,想我可怜不可怜。”这句十八板非常长,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唱得平淡干涩。胡瑞华巧妙地糅合进《小放牛》的曲调,使得这段唱词柔美婉转,充满着自怨自叹的哀婉。在赣剧《玉堂春﹒会审》一场中,当红蓝袍问到初次接客是哪一个时,苏三脱口而出“是那王……”,这时突然意识到,这可能会给心爱的人带来麻烦,于是踌躇起来,胡瑞华在处理这个“王——”字的演唱时把苏三欲罢不能欲说还羞(苏三虽是妓女,但毕竟只接过王金龙一个客,不同于一般惯见风月的妓女)的神态和心理表现得恰如其分。 胡瑞华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吸收青阳腔和弋阳腔甚至民歌的成分,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唱腔,但又不露痕迹,依然保持着浓郁的饶河风格,逐渐形成了刚柔相济、高亢激越、以声传情、朴实动人的独特风格,观众们听得过瘾,又新鲜,称之为“水花调”。她的唱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海峡之声台、南京金陵之声、厦门之声、江西人民广播等电台的播放,飞向全国赣剧爱好者的耳边,影响深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这上十年的时间,在赣剧流行的腹地,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飘扬着胡瑞华那悠扬动听的声音,在农村,许多农民在下地时也不忘随身携带一台半导体,为的就是不错过电台播放的胡瑞华的唱腔,等到胡瑞华的一系列盒带行销于市时,更可谓风靡一时,甚至有的老人在临终前交代亲人:死后一定要把胡瑞华演唱的赣剧盒带放在他们的身边,以便到那边都能听到这优美迷人的赣剧。 在表演方面,胡瑞华同样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她扮演过上百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赵艳蓉、升平公主、秦香莲、陈杏园、柳翠莲、窦太真、色空、江姐等等,而这些形象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胡氏”印记。胡瑞华的表演动作洗练,准确传神,不尚花哨,不拖泥带水,感情真挚,力求从人物出发,在利用程式化的同时,还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赣剧《打金枝》,又叫《满堂福》,因为剧名喜庆,行当齐全,剧情热闹,是下乡演出时观众的首选剧目。剧中升平公主给观众的印象从来就是个“刁蛮”的形象,每次演到《打金枝》和《哭诉》,观众要么觉得解气,要么觉得这个人物可憎。胡瑞华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全新的处理,她认为,这出戏虽然矛盾尖锐,但毕竟是小夫妻之间的闲争吵,只不过是出在了皇家,剧目的主题主要还是着眼于和谐和君臣团结,所以,升平公主这个角色不应该演得让人觉得可恶,否则全剧结尾时夫妻和好就失去了基础。于是,胡瑞华在升平公主上场和挨打时极力表现她的“骄娇”之气,但同时也表露出对郭暧的恩爱。当演到《哭诉》一场,要求父王处斩郭暧时,全然没有考虑事情严重的后果,完全是一副要“出气”的样子,孩子气十足,让人觉得可气可笑又可爱。这个戏成为了胡瑞华的保留剧目。传承赣剧弘扬文化 再比如赣剧《彩楼配》和《回龙阁》中的王宝钏这个人物,虽然是同一个角色,但是由于时间跨度大,胡瑞华在演出时也做了不同的处理,尤其是《武家坡》和《算粮》,她演的王宝钏泼辣而又麻利,全然没有了原来相国千金的矜持:十八年的生活历练,人情冷暖的风霜雨雪,早已把王宝钏锻炼的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所以,在武家坡前挖野菜时,动作熟练而又轻快,反击大姐二姐的羞辱时,把她们打得落花流水。她扮演的秦香莲、赵艳蓉等,比之京剧等其他剧种中的形象更具反抗性。比如秦香莲,面对不可一世的皇姑“为何不近前把我参”的质问时,她不卑不亢地反驳:“论国法我应把你拜,论家法你该把我参”;再比如赵艳蓉在金殿面对秦二世的淫威,她发出大胆的质问:“哎呀呀,皇帝老哥啊,你动不动就要人家的首级,难道你就不怕人家要你的首级么?”当武士们真赶她下金殿去时,赵艳蓉知道自己的斗争即将取得胜利,仍然乘胜追击,“万岁我的儿,武士我的孙,娘与你们结下了冤仇,”并要“恨不得提长枪与你来战。”与其说这是疯话,还不如说这是人物坚决斗争的心声。每当演到这里,观众的反映非常热烈。 胡瑞华的念白也很见功力,比如《秦香莲·闯宫》一场,面对负心的陈世美,秦香莲为了儿女不失去父亲,为了有个完整的家,她不得不委曲求全,声泪俱下地哀求着陈世美,这里有一大段念白,胡瑞华念来字字含泪,声声带情,哪怕是一万多名观众的现场也会鸦雀无声,人们被她的表演深深打动。在最后的一场《铡美》中,当包拯迫于皇姑和太后的压力,决定放过陈世美,把三百两银子交到秦香莲手上时,胡瑞华扮演的秦香莲悲愤地唱出“早知如此我喊什么冤”,仅此一句,绝望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人物的情绪非常饱满,剧中剧外的人无不为此动容。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胡瑞华不断创新发展着赣剧的声腔和表演艺术。在新编古装戏《胭脂狱》中,胭脂游春时巧遇秀才鄂秋隼,一见钟情,回到家中思念成疾。在这里,胡瑞华和音乐工作者为胭脂设计了一段上江调,但是,传统的上江调流水板比较奔放、平直,难以表达出胭脂这个时候的心理活动,同时也不符合怀春少女的身份特点,胡瑞华大胆地创编了一段上江调“二六板”,委婉深情,很好地表达了人物复杂的心境,同时又体现出少女的娇羞之态,显得情意绵绵。这种板式丰富了赣剧的声腔,增加了赣剧的表现力。再如《秦香莲》中的《琵琶词》,一般传统的唱法使用的是孟姜女十二月调,胡瑞华在演唱时,根据人物是荆楚一带人氏的特定身份,大胆吸收荆州花鼓戏和楚地民歌的音调,重新演绎了这段琵琶词,让人听来既新颖,又有地方特色。在赣剧传统剧目《望儿楼》一剧中,胡瑞华扮演窦太真。在别的剧种中,这个人物一般由老旦应工。胡瑞华依然按照赣剧的传统演法来塑造人物,但是,在演唱上,她却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剧中,有一段长达十五分钟的“二黄”唱腔《窦太真在宫院神思恍惚》,这是一段在赣剧中罕见的大段唱腔,由正板、连板、碰板、吟板组成,人物感情极为丰富,对演员的演唱是个极为严峻的考验。胡瑞华根据剧情,从人物和特定情境出发,为了体现人物的年龄特点,她适当地吸收了老旦的唱腔,并借鉴了信河派的一些特点,在正旦的庄重沉稳之外,又使人物平添了几分慈祥。整个唱段起伏跌宕,旋律多变,胡瑞华举重若轻,唱得细腻深沉、层次清楚而又富于变化,很好地体现了人物年龄和身份特点,表达了一个母亲在思念儿子时的拳拳之心。此外,在新编历史剧《西门豹》、《鹿卢剑》等剧中,胡瑞华在音乐唱腔上都有新的创造。她还曾在弋阳腔《江姐》中成功地扮演过江姐的形象,展示了她演唱和表演上的杰出才华。 胡瑞华不仅自己悉心发展赣剧,还专注于赣剧的传承。许多赣剧演员不断拜她为师,向她问艺,以至于赣剧界涌现许多“小胡瑞华”,形成“十旦九胡”的场面,影响颇为深远。著名赣剧演员汪志红、徐晓岚、江玲静、吴华珍、何益萍、李小英等都是出自她的门下,这些人在观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胡瑞华虽然离开了舞台,但她的心依然没有离开赣剧。她不仅致力于培养赣剧的接班人,还经常对上门或打电话求教的戏迷票友进行热心指导,对于近十几年来活跃在乡间的各民营剧团,她也同样予以热切的关怀。她同时担任着几个民营剧团的艺术指导和名誉团长。她不是仅仅靠着自己这块金字招牌为民营剧团招徕观众,而是兢兢业业地悉心指导,甚至有时还不顾年高,亲自登场。胡瑞华,这位生长在饶河岸边,成长于鄱阳湖畔的杰出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她的艺术就如那滔滔的饶河水,浩瀚的鄱阳湖,永远流淌,她的高尚的情操就如那空谷幽兰,永远开放,芳香永驻。 -END- 文章编辑:周文祥文章原稿:蒋良善 图文转载中科医院以品质领跑行业医治白癜风病的专家
|
当前位置: 饶河县 >赣剧表演艺术家胡瑞华饶河声腔第一家
时间:2018-6-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深度品味台湾,必须做的50件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