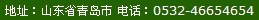|
从东北回来已经两个多月,如果说边疆行有什么后遗症,那大概就是一进屋就想脱掉外套了。可是,南方的屋子像冰窖,脱了外套就冷得慌。当我翻开在东北的一页页日记时,仿佛走进了暖气充盈的房间,坐在烧得火热的炕上,被温暖和幸福环绕。 (一)姑娘们 “姑娘们,你们回来啦!冻着了没?” “姑娘们,来,多吃点儿。” 姑娘们,我们什么时候坐上火车再去饶河? 姑娘们在大顶子山 在团队组建之初,老陶就跟我说了组建团队的要求,业务导向,性别是考虑因素之一。 在这个男生稀缺,但凡是正常男孩子都会受到特殊优待的环境里,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放弃了男生。事实证明,我们是一群汉子一样的姑娘。 每次晚饭,我们总要一个个轮流展现一番,这时候就可见我们每个人的特点了。卓卓每次像是演讲一样,逻辑清楚,声情并茂;彧童一曲校歌,主席风采就迷倒了饶河朋友们;晗之讲话十分耿直,一定要注意她的手势!大爷明明每次一开口就讲得感人肺腑还要偏偏说自己人多说话打哆嗦,好过分哦! 几乎每一场采访都是由我们共同完成的。晗之摄像,应葛摄影,我、彧童、卓卓采访。从晗之架好三脚架,打开相机开始,我们开始运用车轮战术进入采访状态。我先提一些大而宽的问题,然后彧童开始细化,卓卓挑重点,主要问题问完,就需要相互补充,把没有一些细节再完善。三个人都问得差不多时,大爷就会杀出来,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性格各有特点能力又能独当一面,就像老陶对新民晚报的曹老师说:“她们这些人呢,分工上有摄影的,有摄像的,有采访写作的,但每个人其他方面也可以,摄影摄像的也能写,摄影摄像没有人了采访写作的也能上。” 因为有大家,所以我很心安,不管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好地完成。我不为我们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发愁,我只想着我们每天玩得开不开心。 从沈阳到佳木斯的火车上,我还喝着我的AD钙,被大家嘲笑,从抚远返程,我已经可以拿着啤酒跟大家干杯了。不喜欢啤酒的味道,但喜欢大家一起拿着啤酒,啃着鸡腿,在那儿天南海北谈天说地的流浪感。 姑娘们,我们什么时候坐上火车再去饶河? (二)老陶的背影 每一次走在老陶后面,我都想记录下老陶的背影,可总是距离太远,拍得不真切。 老陶的背影 1月9日05:30,经过飞机、火车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佳木斯,距离我们的目的地饶河还有近6个小时车程。 拖着行李,走出火车站,天还没亮,老陶带着我们走进附近的一个酒店,在酒店大堂暂时休息是老陶的预定计划。 意料之中的,老陶用他的无敌魅力说服了小姐姐收留我们,我们一个个拖着行李箱,跟着老陶进入酒店,踩在脚上的雪弄脏了酒店的地板。把我们安顿好后,老陶背着他的万能书包去买车票、物色吃早饭的地方,我们在大堂的暖气里为即将到达的地方兴奋。 大约一刻钟后,老陶带着寒气推开酒店门,兴奋地告诉我们,从外面看着黑漆漆的,车站里面已经人声鼎沸。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愧疚。 从我成为传新的主编开始,遇到大大小小的难题都会找老陶。每一次老陶既会安抚我的情绪,也会告诉我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我已经习惯了老陶以一个万能的角色存在。因为老陶的事无巨细,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在老陶庇佑下的安逸。 直到这个早上,我才突然意识到,老陶只是我们众多老师中的一个,难道仅仅因为他熟悉所有的事情,就要帮我们做这么多吗?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理所应当地享受老陶的照顾呢? 出发前,老陶说:“我一定把你们所有的吃住都搞好,你们只要专心采访就可以了。” 事实上,老陶不仅管了我们的吃住,而且每一次采访的“渐入佳境”几乎都是由老陶推动的。养蜂行业背后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锋,饶河旅游业发展的困境,朱翥职业选择的原因······ 第一次体会老陶采访渐入佳境的套路是夏季安徽采风采访彭镇长,老陶对我说:“陈静,让他吐吐口水。”那次的采访因为这句话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见证老陶使用这一招,并在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这一招的作用。从安徽采风之后,我很喜欢问老陶问题,因为老陶从来不吝惜于分享做某件事的原因,分析每一件事情背后复杂的背景,每一次问老陶问题都会有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 1月9日下午,我们终于到了饶河。吃完午饭后,老陶说去饶河街头走走,我跟着老陶去了。我们沿着通江街,走到百合广场、县政府、客运站、博物馆······在沿着迎春街回酒店的时候,我看到老陶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下来,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在街上的时候他有时候带着帽子,但大部分时候是不带的,于是问他原因。 老陶说:“因为带着羽绒服的帽子视线不好,所以我喜欢我那顶绒线帽。” 在来饶河之前,我们还嘲笑了老陶去年在大庆时带的那顶绒线帽,却不知道老陶的帽子还有这样的讲究。我是被震惊了。 这样的细节实在太多,不问则已,一问惊人。 逛一圈饶河县城,我大约只记得饶河有一条贯穿的通江街,沿街有很多重要的机构这一点。而老陶根据这一圈,能够在第二天调整行程,在我们从口岸回来后,再去博物馆;在客运站,记住饶河跟各地来往的车程、班次,并且通过车站判断车站的吞吐量。还有更多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从去新民晚报、上海市口岸办,到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再到饶河和抚远的街头,我一直走在老陶的后面,跟随着老陶的脚步前进。走在老陶后面的时候,我拍了很多张老陶的背影,但没有一张让我满意。 老陶的背影是变化的,会因为照顾我们的速度而停下来等待,会因为抚远易滑的街道变成小脚老太太的模样,会因为生气而不再回头看我们,但他的背影也是不变的,每一次都步履匆匆,每一次都坚定有力,每一次都朝着既定的目标。我没有拍到完美的照片,但已经在心里留下了底片。 在老陶的教学生涯中,与众多的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交集,但在我的大学经历里,老陶是唯一一个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 老陶笑我每次说“谢谢您”都不真诚,这次我要用最最最最最最真诚的语气对老陶说:“谢谢您!” (三)采访这件小事 新闻人的笔下是惊涛骇浪,我想我应该越来越谨慎。 认识的深度决定了采访和写作的深度。 到葛老师家拜访 东北的所有采访几乎都是温和而没有悬念的,这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失去兴奋感。 第一场采访在黑蜂管理局,采访企业家侯树建和专家唐临玉。我和彧童先采访完侯,再去看大爷和卓卓采访唐,因为已经听过候的介绍,所以对两方的信息有对比,发现了一些不能对应的部分。我们后期没有进行严密的求证,但通过其他渠道有一定的了解,初步判断候说了一些假话。 这件事加上之前安徽采风的经历,我一次次体会到“真实”这个词到底有多远。我们获取了事实,但这些信息可能是:部分事实、修饰的事实、单方叙述没有经过求证的事实······ 这让我很害怕。暂且把我自己定位为新闻人,定位为记者,我们的受众通过我们的文字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传达的信息构建了他们的认识。如果我们采访不到位,如果我们在传达的过程中有私心,那么受众知道的将是什么样的世界? 新闻人的笔下是惊涛骇浪,我想我应该越来越谨慎。 27日凌晨一点过,我一边和大爷讨论辱母案,一边写感想。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南周记者的报道对于受众对事实的理解和舆论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讨论这个事件本身,也讨论南方周末的报道,还讨论法制、舆论等等。即使是坐而论道,我也为这个讨论欣喜。 去葛老师家里拜访的那天我有些触动。葛老师是伊玛堪传承人,我们在第一次采访她后决定再去家里拜访一次。葛老师很善于表达,不管是故事还是观点都很有感染力。第一次采访完葛老师时,我其实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一些困境。但是在第二次采访时,我觉得葛老师的形象不同了。在第一次采访时,我仅仅把她作为一个“传承人”来看待,更加在意她的身份,第二次,因为到了她的家里,也见到了她的丈夫,除了正式采访有了很多其他的体会,我觉得这时候她的形象从“传承人”变成了“人”,比之前更加丰富和饱满。 其实触动我的只是一个小点,就是葛老师跟丈夫的相处,但是这一点打破了她在我心中单一的“传承人”形象。我想,采访是应该从“人”开始的,了解一个人不仅仅是通过这个人本身,需要多方面去观察,对人的了解真难。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这时才深刻地体会到。 我们在东北的采访平静无波,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陶的实力支援。在饶河旅游局采访已经快要结束时,老陶问了王局长饶河旅游业发展的困境。老陶对交通、附近城市的情况很了解,点出了饶河在旅游业发展上与周边城市区县相比的不足。王局长这时大概有遇知音的感觉。也许每一个采访对象既想对记者有所保留,却又渴望被记者触碰到心底深处的想法吧。一场不深入的采访,不管是采访对象还是记者都是不满足,找不到成就感的。 (四)读书与行路 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我喜欢在乘火车时看地图,随着火车的轰隆声,地图定位沿着铁路线路过一个个城市,仿佛对构成这个世界的网络,我又多了解了一分。我一直无法忘记第一次乘火车翻阅秦岭时的欣喜和激动,那是秦岭啊,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秦岭—淮河”的意义我们可是背了整整六条啊。 上初二时,政治和历史都在讲改革开放,这让我很想看看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的深圳到底是什么样子。爸爸妈妈带我去了深圳,这是我第一次出川。尽管深圳并没有带给我多少惊喜,可那个想用脚步丈量书本世界的种子埋在了我的心中。 在东北,那种好奇、兴奋、激动又出现了。 当我们乘着汽车路过一个个农场时,历史书上缺失的那段历史终于被弥补;当看到冰雪覆盖田野,白茫茫一片的时候,“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突然出现在脑海里,众人奔散,食尽鸟绝的悲凉铺面而来;当我们出饶河,往抚远行去时,一望无垠的三江平原以一种浩然之势出现,这时候才终于明白地理上分析东北农业的区位优势,才明白商品粮基地,广袤的三江平原是什么概念。 在东北,我们有多种多样的经历。在小南河实际体验了“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在东北铁锅炖围着大铁锅吃炖鱼吃大饼子,黑鱼狗鱼大马哈鱼,各种鱼都吃过,也上过炕,感受过炕上的温度,最遗憾要数没有在二人转狂热爱好者老陶的带领下看到二人转了。 在东北,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人。有计划内计划外的采访对象,有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有偶遇的酒店大爷、上大学生,每一个人的形象都如此鲜活,在我们的边疆行里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也会学着衣叔叔的笑容和语气,对晚辈们说:“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五)乌苏里江长又长 天边的那轮圆月静悄悄地挂着,影影绰绰望不清轮廓,朦朦胧胧的月光洒在冰封的乌苏里江江面,更添了几分清冷。眺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我的心里变得很平静。 静静站在乌苏里江江面 在四排乡采访完尤小坤,唐哥带我们到乌苏里江上玩,有一个爷爷为了让我们去玩特意准备一番,准备好一直等着我们。 冰滑梯、冰陀螺、冰爬犁,我们在夜幕里体验了冰上游戏,玩得很尽兴。我一直非常害怕下坡,坐汽车都怕,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冰滑梯。在下滑那短短几十秒里,在速度与寒冷的刺激下,可以忘却所有的思考,压抑的情感也得到释放。 清冷的月光洒在冰封的乌苏里江江面,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眺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墨蓝色的天空,像柔和的月光,像冰封的江面,仿佛是寻觅已久的期盼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们离开时,邀请那个爷爷跟我们一起乘车,他拒绝了,他要一个人把我们刚刚玩过的设施拖回家里去。他不认识我们,却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在这里准备,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内心的感情。 除了这个爷爷,还有小南河乡的村长、帮我们挑衣服的阿姨、给我们做饭的阿姨,有那么多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受到打扰。那一刻,我想,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对我们这么好,我都很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准备了这样的体验。因为有他们,我们的边疆行才会充满温暖与乐趣。 感谢姜爸爸、马哥、刘姐、衣叔叔、唐哥、王老板、任局长、强哥在饶河期间对我们的关爱和帮助,感谢远在美国的姜颖学姐。因为有学姐,才有了我们与饶河的缘分。在饶河的日子很美好,即使有采访任务在身,也是轻松愉悦的。我对饶河的所有温暖记忆都来源于饶河的亲人们,感恩。 在回县城的路上,我说,今天的感受就是采得开心,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什么都开心。这句话实在是太朴实了,太粗糙了,但这也是我在饶河最真实的感受。 到抚远时,我们已经有点电量不足,渐渐开始消极怠工了。但冬捕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的。在抚远抓吉镇,去看冬捕的途中,汽车陷在雪里,进退不得,汽车在雪地里打滑咆哮,车下是冰封的乌苏里江。 我们面临要不要继续去看冬捕,如果不去又该怎么安全出去的局面。我有点好奇又有点害怕。车轮碾过江面厚厚的积雪,留下粗犷的车辙印,看着车窗外的白色,我想起了电影《孔子》里的一个场景。 孔子一行结束周游列国的行程,在寒冬腊月赶回鲁国,他们赶着马车驶过一条冰封的大河,冰面断裂,载着满是书籍简册的大车倾覆。颜回有自救之力,但为了捞出水中的书籍,他一次次游向江心深处,一次次带着一捆捆书籍游出江面,最后因为体力透支,他沉入了江底。 这个画面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于是我脑补了我们掉进冰窟窿里的场景。想到我们可能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也算是一种带着刺骨寒意的浪漫。当车驶出雪地,在江岸的老房子区呼啸着时,我还心有余悸。 在乌苏里江上,我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也偶遇了生命的危险。回想起来,这段旅途最美好最惊险的经历都与乌苏里江发生了关联,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饶河开工第一天,我们站在博物馆凝神细听《乌苏里江船歌》的画面,高亢悠扬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响起的是一段关于乌苏里江的故事。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 船儿满江鱼满舱 啊朗赫拉赫呢哪雷呀赫啦哪呢赫呢哪 出处:人民网来源:上海大学学生陈静 编辑:高远 欢迎添加小编北京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是哪家什么偏方能治白癜风
|
当前位置: 饶河县 >饶河乌苏里江长又长上海大学生边疆行
时间:2017-1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收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饶河吃货有文化
- 下一篇文章: 饶河县召开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推进会议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